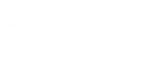炸子鸡”,无论是赛道的抢手度还是头部公司的“吸金”能力,都佐证了这一点。究其原因,面对集采常态化、医保谈判控费等政策,核药是其中难得的高壁垒、高增长赛道。
诺华是核药领域当之无愧的“先行军”。从2018年开始,诺华前后斥资近百亿美元在核药赛道“买买买”:先后获得RDC治疗药物177Lu-dotatate、177Lu-PSMA-617,并因此坐实了全球RDC领域的头把交椅,后又在2022年将第三发子弹瞄准了FAP(一种核药靶点),对核药的关注持续升温。
诺华的重仓和后续所展示出的“钱力”,以及国内政策利好频传也极大地鼓舞了行业,中国资本市场对核药的投资热情也就此被激发。
自2022年3月Pluvicto获得FDA批准以来,诺华的核药产品Pluvicto(177Lu-PSMA-617)——用于PSMA阳性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三线治疗,已成为名副其实的“现金奶牛”。根据最新财报数据,Pluvicto Q3销售达2.56亿美元,前9个月累计营收达7.07亿美元,不出意外今年将卖到10亿美金,由此跻身重磅炸弹行列。
Pluvicto并不是昙花一现的现象级产品,诺华另一款核药产品治疗胃肠胰腺神经内分泌瘤的产品Lutathera在2018年初上市以来累计销售额已经超过20亿美元。
在今年进博会“前列腺癌靶向PSMA诊疗一体化发展论坛”上,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副院长、泌尿外科科主任薛蔚教授向36氪透露,目前177Lu-PSMA-617正在国内多个医院开展临床试验,主要针对晚期和转移病人。据他介绍,这是唯一一个到了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(CRPC)阶段还能延长OS(总生存期)的药。
为什么是前列腺癌?据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核医学科主任石洪成教授解释到,目前它在该领域“最成熟、证据最确凿且大家最认可”。据薛蔚介绍,目前中国前列腺癌发病率呈显著增长趋势,其主要原因可能包括人口老龄化、生活方式改变以及筛查方式的普及。
据统计,2022中国前列腺癌发病人数约12.6万,死亡人数约5.6万;美国前列腺癌发病人数21.7万,死亡人数3.5万,存在显著差距。薛蔚解释到,中国的前列腺癌发病率低并不低,主要还是筛查做得不仔细,往往来就诊的病人大部分都已经骨转移了,才想到可能是前列腺癌,“这些病人的治疗OS跟早期诊断出的病人起码要有10年以上的差距”。
转移性CRPC是前列腺癌疾病发展的终末阶段。前列腺癌的生长和进展都依赖雄激素,所以目前前列腺癌的治疗前列腺临床试验,主要是通过雄激素剥夺疗法,阻断体内雄激素(睾酮)的供应。但对一部分患者来说,即便经过雄激素剥夺疗法治疗后,患者体内睾酮水平已经很低,但肿瘤却仍在不断进展,成为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(mCRPC),癌细胞扩散至前列腺以外。即便是末线,mCRPC依然拥有较大的患者群体规模。有数据统计,它在所有前列腺癌患者中该群体占比大约为8%。
据了解,mCRPC患者生存率不高,5年生存率仅在30%左右,临床需求尤为迫切。诺华核药所靶向的PSMA是一种新的肿瘤标志物,在超过80%的前列腺癌细胞表面高表达,而靶向PSMA放射性配体疗法(RLT)具有精准、高效、副作用小、能够实现诊疗一体化等优势,已成为治疗前列腺癌尤其是存在多处转移患者的重要方法。
据了解,由于具有较低的肿瘤突变负荷+冷肿瘤属性等诸多原因,免疫疗法针对mCRPC也无可奈何,哪怕是PD-1中的王者K药,面对前列腺癌也是束手无措。这一市场格局下,诺华对核药也寄予了厚望。
据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核医学科主任赵晋华教授介绍,放射性配体疗法(RLT)的原理是与特异性分子结合的放射性核素,通过跟靶细胞表面高表达的生物标志物特异性靶向结合,定位到全身各处肿瘤病灶,利用辐射杀伤靶细胞。
通俗地来理解,“相当于我们拿导弹去打一个敌人,导弹可以精准识别(由放射性核素的特异性结合),先用显像核素去侦查这个病人有没有表达,如果有表达的话就会挂一个核弹头(治疗核素β射线)去摧毁这个病灶,实现治疗效果。”
以177Lu-PSMA-617为例,它能与肿瘤细胞表面表达的前列腺特异性膜抗原(PSMA)结合,同时177Lu能够释放β射线,起到精准靶向杀伤肿瘤的作用,相当于给177Lu安装了一个导航系统,让药物最大程度地富集于前列腺癌病灶上,进而增加治疗效果。
薛蔚指出,放射性配体疗法还能利用不同的同位素与不同配体组合,有望用于多种癌症的诊断、监测、治疗,应用前景广阔。据诺华中国医学事务部负责人兼首席医学官吴铃介绍,诺华正在推进广泛的RLT组合,探索新的同位素、配体和联合疗法,除了前列腺癌,还要进入乳腺癌、结肠癌、肺癌和胰腺癌领域。
如何来理解这种“随机组合”?放射性配体疗法的分子结构其实与ADC(抗体药物偶联物)的分子结构类似,大多以配体、linker和同位素组成。使用不同的医用同位素,可以具备显像或治疗等不同功能,部分同位素兼备两种功能;配体则是能将放射性核素递送至体内特定部位的非放射性成分,类似于“导弹”。
放射性配体疗法可以只更换核素部分,在相关靶头和Linker都保持相似的情况下,形成诊疗一体化的产品,如连接氟[18F]、镓[68Ga]等形成诊断产品,连接镥[177Lu]、锕[225Ac]形成治疗药物。
另外,不同结构的配体对后续药物的开发有着重大影响。据了解,目前放射性药物最常用的配体是小分子多肽,由于其分子量较小、血液半衰期较短、代谢通过肾脏等因素,所以它的肿瘤穿透能力较强、血液毒副作用较低,但具有一定的肾脏毒性;此外,小分子多肽还难以筛选到高亲和力、高特异性的分子。
像诺华两款药物的多肽是在天然多肽的基础上,由科学家不停优化筛选出来的。如靶点为生长抑素受体的Lutathera(镥氧奥曲肽),奥曲肽是一种人工合成的天然生长抑素的八肽衍生物,药理作用与生长抑素相似。天然的生长抑素肽激素与SSTR具有高亲和力,但其生物半衰期短,不适合用于显像或治疗。而人工合成的生长抑素类似物既保持了对SSTR的高亲和力,也同时延长了生物半衰期。
另外,还有一种常用配体是抗体,普通抗体由于分子量较大,导致其组织穿透性差,多量滞留于血液中,如果用于治疗则可能导致血液毒性;而且抗体的半衰期长(可达数天),影响图像质量且导致检测间隔长,但比较容易筛选到高亲和力、高特异性的分子。
还有一种是纳米抗体,它集合了小分子多肽和抗体两者的优势:在既能有较强的穿透能力下,也能筛选到相对高亲和力前列腺临床试验、高特异性的分子。
目前以放射性配体疗法为核心管线,国内已出现了大量创新公司,除了恒瑞医药、远大医药等老牌药企引进相关项目外,也有智核生物、辐联医药、核欣医药、艾博兹医药、诺宇医药、晶核生物、核舟医药等一批新锐核药企业先后成立,并斩获了较高融资。
即便有这么多创新力量加入,成功的放射性配体疗法仍然寥寥无几。高研发壁垒显然是关键原因,产业链配套和目前的严监管都给要贸然入局的后来者竖起了一道“高墙”,行业并未能设想的那样“卷起来”。
首先,从研发角度看,放射性配体疗法所需的核素、配体都有相应门槛。在核药生产环节,核素一般依托于大型核反应堆或回旋加速器产生,具有放射性,其建造和运作都有较高的技术门槛和异常严格的规定;另外,是核药涉及复杂的放射性示踪技术及放射性检测技术。至于配体,要获取高亲和力、高内吞还能保证生物半衰期的配体并不容易。在此基础上,放射性配体疗法的成药也是壁垒。
其次,在产业链端,核药有自身特点,与普通的药物可以长时间保存不同,核素半衰期非常短。具体有多短呢?就拿现在临床试验中常用的放射性核素来说,Y-90半衰期2.7天、Bi-213半衰期45.6分钟,Pluvicto选择的Lu-177半衰期稍长,但也仅有6.7天。这也导致很多核药无法提前量产和长距离运输,对药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,不仅要能够生产核药,还要保证能够及时配送。
而在监管端,目前政策正在逐渐对“核药”松绑,不过也依然存在缺乏学科建设的标准、人才培养的不足、医保对相关药品覆盖不够等方面的问题,都需要逐一去解决。
此外,核药的临床使用亦有门槛。这除了临床医生的参与,也需要核医学科的配合。石洪成教授告诉36氪,就放射性配体疗法而言,治疗专业性很强,且相应的法律要求这一定要用特殊的病房,所以病人早期一定要放在核医学的病房来管理,当治疗已经达到非常安全的情况下,病人才能再回归到普通环境中,譬如到泌尿外科进行综合性的整体的再治疗,需要多学科的合作建立新的诊疗路径,才能实现新疗法的推广和普及。
随着放射性配体疗法不断涌现新的医用放射性同位素,也需要更多的技术支持和证据生成以支撑推进核医学相关领域标准、规范的形成与完善。为此,长三角核医学技术应用联盟应运而生,相关各界将共同探索核医学产业的发展之路。当肿瘤有了“核”武器核药成为诺华的“新王牌” 行业观察
版权声明
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,不代表本站立场。
本文系作者授权发表,未经许可,不得转载。
本文地址:http://www.zhuanqianla.cn/fumianshanchu/2023-11-10/4839.html